
2020-09-25
“Monet”属于谁?——美国法律体系的入门书 (第二版)
John A. Humbach/著 刘汛/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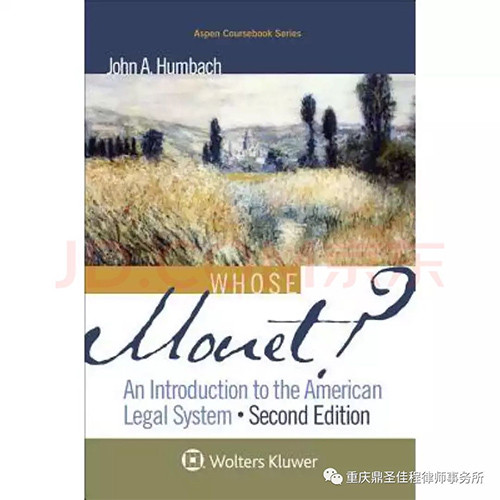 第九章:律师与法院如何运用先例 正如我们在前两章中看到,大量的美国法律并没有编纂成法律,但是以判例法(司法先例)形式留了下来。即使法律是法定的,法院极其重要的法律解释也不仅限于“法律”本身,它们还能显著地改变法律的含义和司法作用。然而,不要以为律师处理这些先例的任务被限制,限制着他们只能去寻找看上去可以适用的先例然后提交给法官。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 首先,个体的先例产生了不同的种类——有些强大、有些弱小、有些直戳要点、有一些没太大关联、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有些先例被认为是“强制性的”,它们必须被遵守(理论上),然而其他先例被说成仅仅是“有说服力的”。最重要的是,先例的含义频繁地被其他先例的理由所影响,这些其他先例能更准确地指出了美国判例法存在于判例主体里,而不是在个体案例本身里。的确,在那些任何你可能找出来支持给出的结果的判例,通常在某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的先例,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能够貌似可信地说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评估和使用先例中出现的这些复杂性,使先例的分析工作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技能之一,你会在法学院里学到它们,尤其是在第一年里。在进校数月内,你阅读案例的目的是为获得一种感觉,一种律师如何类推事实和结果很相似的案件的感觉;一种他们如何分辨看似类似、实际上并不一样的案件感觉;一种他们综合案件类型来发现和运用法律原则的感觉。在本章,我们将首先看到法律分析(识别类比、区分和综合的过程)涉及到什么。我们将考虑两个普通法的核心特点,即是说:它作为法律系统基本的稳定性,以及反应变化的内在的灵活性。乍一看,这两个普通法的核心特点可能看上去是直接相互矛盾的,但合在一起,它们就给了普通法持续性和弹性。 普通法的稳定性——遵循先例 美国法院令人担忧的学说莫过于:无视以前所有的判决和法规,不顾已确定的在先原则,而自行做出决定。 ——大法官Joseph Story
基本上,普通法的稳定性建立在先例原则上,但它更精确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最简单的概念里,跟随先例意味着在同样(或类似)的情况下,重新做一次你曾今做过的决定。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些事情第一次对我们有效,我们很可能会再尝试一次。这种先例的使用,通过赋予“从过去的经验里进行学习”的实际价值来帮助我们生存。先例的法律原则确实是这样,甚至更多。Chancellor Kent,一个自美国普通法形成时期被高度评价的学院派法学家,给了如下三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先例应该被遵循: (1)一个具有法律要点的庄严判决(它们出现于任何既定案件中),对类似的案件成为一种权威,因为它就是我们能掌握并适用到主体的法律的最重要证据。只要该判决未被推翻,法官一定得一直跟随它。除非,它被证明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法律被错误地理解或者被错误地适用。 (2)如果一个判决经过庄严的讨论和成熟的审议被做出…社会有权利把它看成法律解释的公正宣言,它可以规范他们的行为并约束社会。 (3)通过这些规则(专业人士向前来咨询的人提出安全的建议),的名气和稳定性,人们通常会信心满满的去冒险、去购买、去信任以及去相互交易。 换句话说,太多法律的灵活性和易变性意味着没有人能够规划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法律规则框架,包括合同、侵权责任、公司治理以及类似的法律规则框架。人们不能充满信心地投资、制定一个长期安排或者成立一个雇佣数千名员工的企业。大多数人会发现购买房子,甚至购买汽车都很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法学学生不能获得学生贷款。这样的担忧会产生这样的表达:“法律…与科学不同,它不仅关系到判决的结果,还关系到稳定性,为了稳定,它将频繁地牺牲实质性的正义”。 牺牲正义?看上去真是一个为了稳定性而付出的糟糕代价。然而,稳定性也能推进正义,它有助于法律内部的一致性。一致性并不仅仅是整齐的问题(整齐可能一点也不重要)。理论上讲,正义需要法律具有稳定性,很多人相信法院应该“对类似的案子类似处理,对不同的案子不同处理”。比如说,假设两个人在类似的环境下做了同样的行为,如果第一个人必须承担巨额的损害赔偿金,而另一个人只是被释放,因为一个案子是周二诉至法庭,另一个案子是周五诉至法庭,或者一个在去年起诉,而另一个在今年。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当然条件可能会变化,如果先前的判决明显是错误或者过时的。那么“平等”可能不得不屈服于其他的法律问题。然而,这是判例学说的一般性概念,当缺少改变的理由时,司法判决一般应与法院在之前案例中运用的法律和规则是一致的。正如大法官Antonin Scalia所说:“平等对待是人类精神的推动力,不能被高估”。 可能大法官Scalia在这点上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点。特别是,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认为先例在后面的案件中能真正的“约束”法官,那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取而代之的是“法律之下的平等”仅仅需要一种程序上的公平,即,类似情况里的当事人有权获得相同的法律程序,尽管没有达到同样的法律结果。这个观点即是:如果每个案子尽可能地被客观公正的审判,每一个人有公平的机会听取意见和表达,这就是足够的平等来达到公正的目的——或者,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了。 然而,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但美国司法体系深深地致力于普通法判例学说,这一学说的象征被认为是“遵循先例原则”,它字面上意味着“做出决定”。在遵循先例规则的严格实施下,法院受制于它自己在之前的判决中做出的所谓的“判决理由”,当然,该法院先前的判决理由的效力也优于现在的判决理由。判决理由涉及到法院的意见部分,这些意见具有逻辑必要性,用以支持和证明案件中的维持和判决,即,谁胜诉的判决。虽然附带的解释材料通常也出现在司法意见中(比如,假设和阐述的讨论),但这些离题的“咨询意见”以及其他偏题的法律评论并不是判决理由的一部分。因此,遵循先例原则并不需要在后面的案例中遵循这些“咨询意见”。 司法意见力,这个非“理由”的内容被称为“附带意见”,或者有时候简称为“意见”。即使附带意见不是必须被遵循,但通常它们也会被尊重,经常被引用或者被辩护人或法官适用,好像它已经是“理由”的一部分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法院倾向于这样做,那么它可以毫不费力的驳回附带意见。当法官抛开“意见”时,他们很少表现出像推翻先例时那样的严肃和勤勉。因为附带意见通常不太受到尊重,你会发现几个关键的法律活动之一是精确地判断哪些是法院意见的部分、哪些是理由部分、以及哪些仅仅是意见。通常,这并不容易察觉到。一位“司法杰出人士”有一次被他同事问及其中的区别,他回答道: 规则确实很简单,如果你同意其他法官的话,你就说它们是理由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意,你就说他们是附带意见… 无论如何,一个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禁止法院否决他们自己的判决)并不体现在美国普通法里,尽管据说它在英国也适用。案例原则的效力仍然不能被低估。如你所知,在美国普通法中,法院先前的判决存在明显的“引力”,牵引着后产生的判决,即便判例的效力随着诸多因素(比如法院的等级、案例的年份、法官的声望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上述现象和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的不同之处在于,严格的原则对待个案的判决理由从本质上讲就是law per se(译为“法律本身”,字面上的“强制的”权威),然而,更务实的美国遵循先例原则对待大多数案例权威,实际上就像程度上或多或少的 “被说服的”权威,。然而,请注意,大部分案例权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高等法院审理案件中,等级制度或者一组在相当长时间展示出一致性的相关判决的诉讼理由,就像是“法律”一样。
先前的法院判决如何约束后面的法院? 尽管遵循先例原则作为美国法律的一个关键特征被大家接受,你应该注意到它并非不存在严重的挑战。毕竟,实际上,人们如何才能想象,具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真实的法官能被书写在一页一页纸上的和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文字所限制呢?的确,为什么法官应该被限制呢?在这一节中,我们会简要地考虑一些挑战遵循先例的原则并考虑为什么他们总体上不被广泛的接受或信赖?首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暗示了关于法律性质本身的严重问题:法律本质上只是一个特别的、在过去被法律统治者公布的规则集合?还是它实质上包含了更多?更简单的说,法院有权“制作法律”吗?或者它的工作只是找到和遵循法律?注意这些并不仅仅是枯燥的哲学问题,这些观点远未得到解决,这些对代理人和他们每天面对的现实案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名法官认为其是否适合“制作新的法律”并适用它,这对律师的具体客户很可能意味着胜诉或者败诉的区别。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有一些著名的法学思想家,他们断言法院不应该把他们自己约束于先例中,至少不能约束得太紧。例如,伟大的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提出它就像“活着的政府靠着死去的人”——他的意思并非恭维: 我有学识的同胞们,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应该是最后一个低估它的人,我已经从年鉴中完成了我问题的分享。但它容易将我们领入歧途。就法律依赖学习而言,它就是所谓的“活着的政府靠着死去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毫不疑问,生者应被管理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给予我们自己的词语,并限定了我们想象的范围;我们不能丢下它。在清楚展现我们现在做的事和过去做的事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逻辑上的愉悦感。但只要它可以,它就有权利对自身进行管理。它应该经常被回忆起,“过去”存在的历史连续性并不是一个义务,而仅仅是种必要, Homes是马塞诸塞州最高法院和后来美国最高法院一名极具影响力的法官。他也是普通法评论家和杰出的法律获奖者。他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开创者之一,该运动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并在二十世纪时蓬勃发展。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 当我们讨论法律时,让我们都现实一点。普通法并不是真正、真实“存在”于客观物体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放在某处的规则体,等待着法官发现并运用它们于具体案例中。引用Holmes自己的话,普通法不是“一个天空中无处无在的徘徊”,普通法更像是法官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的存在,仅此而已。 法律现实主义的目标被他们叫做“法律形式主义”、或者“机械法学”。关键的形式主义概念是法官永不该肆意地制造法律;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发现法律是什么,然后再应用。十九世纪,一位法律界的引领者——John Austin嘲笑这个概念——法官仅仅“发现”法律,并被那些把普通法视为“自然产生的、不可思议的、时不时在法院存在的东西”的法官称为“幼稚的谎言”。相反,形式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法官篡夺了立法者的权力,那他们就是无法无天的变节者,除非法官严格的附在已经存在的法律规则上,然后把这个标准继续传递下去。 虽然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这样称呼自己(它一开始是一个滥用的术语),他们对待司法角色的态度很清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是我们今天称作“法官主观能动主义”的审判风格,该风格的反面是“严格解释主义”或者“司法自制”。今天的律师在法律评论中、甚至在参议院确认的听证会上,针对司法主观能动主义(前述现实主义者的核心内容)是否恰当的讨论仍然十分活跃。 第二个法律现实主义挑战遵循先例原则主要的点在于,它太激进了。这个意见甚至不可能在具体案件的法院判决中被法律规则所限制。这个争论是这样的:现实中的法官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决定案件,而法律规则并不能阻止它。一个法官在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不能被之前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限制。首先,因为语言和含义从来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在后来,法律现实主义和他们的继任者在一场被称为“批判性法律研究”活动中说,法律和其应用从根本上说总是不确定的。 但根据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这里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要点。判例的各种本质留给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纬度,让他们按照其希望的方式来审理案件,因为“冲突规则将被运用在几乎每一个诉讼案件上”,“在第一个地方适用的规则选择并不被法律所决定”。“依赖于法官在案件中如何理解被视为先例的材料,她会提取不同的、通常在个案中会产生冲突的法律规则”。领导批判性法律研究学者之一——Duncan Kennedy曾今提出一个技术列表,法官能避免先例的适用,只要他们发现其中存在问题。然而,实际上法官还是可以让案件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进行。
因此,如何使先例具备约束力? 法律现实主义和“批评者”做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那就是法律不能像形式主义那样来确定(以及当代限定解释),但他们做过头了吗?大多数律师和法官可能同意这点(除了批判者以外)。具体来说,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几乎肯定是不切实际地低估了大多数法官的迫切的主观能动性。法官作为被赋予关键制度性角色的人,他们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沉迷自己独特的“权利”概念。在现实中,他们似乎非常关切两个问题:了解先例是什么并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在先例中找到的法律——不是作为他们自己偏好的面具而是作为法律。 当法官坐下来开始书写意见时,比起制造法律,更可能的是,他们发现自己进入到一个“发现”法律的思考过程。法官希望引用并(缺少一些不这样做的强有力的理由)遵循任何合适的先例。甚至当先例中有一个“空白”,需要法官做出决定时,他们很少像立法者那样遵循着成文法的规则“制作”法律。相反,正如Ronald Dworkin中肯地意见,真实的、处理这些“开放结构”领域的法官通常根本不会发明新的法律,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尽量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原则,在先前的判例中“具体”或者“模糊”它们——不仅仅是在具体案例中,而是在潜在的、法院管辖的所有司法判决里。 即使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Holmes,在履行他的法官职责时,他并没有拒绝先例的吸引力。他就像其他法官一样引用了很多先例,用这些先例证明自己判决的正当性并表明判决遵守法律要求。以及在Holmes实用主义传统中,具有决定性的现代司法思考者Richard A. Posner法官的观点很明确: 一个制作判决的人,不仅必须考虑在案件中所处理的实质性正义,还必须得维持包括大量先例的法律体系。 然而,Holems和其他的法律现实主义者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点:普通法不能理所当然的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创造的管理体系,但是,它可以依据每一个选择和行为,这些选择和行为是个体——律师和法官——赋予它特殊的内容以至于能够在具体案例中被适用。在较早的脚注中会发现,这里经常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一个关于法律问题“单独的”答案,但可能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一个不太严格的遵循先例的版本给我们一个较为权威的正确回答,它让我们可以规避掉错误答案,同时,当这里有一个不错的书面理由,让人相信旧有规则已经过时时,它仍然把灵活性留给了新的、更好的决议。 最后,你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在具体案件中,很多或者大部分实际情况(生活、法律和其适应性)是十分清晰、没有太多争议的。然而,这种情况就不需要用到律师的时间和技能,律师通常使自己集中于那些重要的法律问题或者含糊的事实上。因此,尽管从实践律师(或者法学生)的角度上看,法律存在大量的易变性和延展性,但法律体系的运作毫无疑问是个好的方式,它更稳定和可预测,比那些时而关注法律不确定性的人好得多。
普通法的灵活性 法治没有更好的理由了,所以将它放在亨利四世时期,这真令人作呕。更令人作呕的是如果理由已经消失了很久,而法律还是坚持简单地盲从于过去。 ——Oliver Wendell Holmes
然而,超过一个世纪,被建立的先例用来解决许多重要的争议,这些争议来自于法院,通常遵循这些先例会给普通法带来大量稳定性(有时候也称为“僵化”)。甚至这种事情经常出现:一个争议被带到法院面前,但这里并没有任何合适的先例或者法规,或者这个争议包含了明显“有区别的”因素,因此最贴切的先例和法规将带来一个不具备吸引力的结果。在这些“开放的结构”的领域中,仍然能够看到普通法的持续灵活性和易变性。然而,法院对遵循先例原则的坚持倾向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它也为普通法不断适应新环境和遭遇的挑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本节中,我们会看到法院如何通过运用新颖的方式运用旧有判例,来合成新的法律。 为了引出讨论的话题,让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案件。想想一下Anna Jones小姐拥有一只狗,大家都知道这只狗咬人。他的房东Errol Brown先生知道这条狗以及它的癖好,但是他认为他的租客选择宠物是她自己的事。无论如何,他没有做任何事。一天,只有五岁的小Sarah Gardner拜访Jones小姐,这条狗咬了Sarah。由此造成的伤口需要缝几针。Sarah的父母咨询了律师Ellen Dodson Esq,她建议他们起诉。由于Jones小姐没有钱(我们称之为“审判证据”),Dodson律师也建议他们将本案唯一的“有钱人”——房东Brown起诉至法院。因此,他们指示Dodson代表Sarah这样做。 假设这里没有法规规定房东是否需要对租户的狗伤人承担责任。Dodson小姐(还包括Brown的律师,最后,还有法院)必须看看普通法。他们能在哪里找到普通法呢?如果他们只需要关注过去得到司法认可的行为标准,答案相对的简单。他们能在法律图书馆里找到这些答案,或者通过电脑辅助的法律研究服务,比如LexisNexis或者Westlaw。但是假设并没有这样的案例,本州的法院也没有说过是否房东需要对租户的狗的伤害行为负责。换句话说,假设Sarah诉Brown的诉讼是律师们所说的“第一次出现”的案件。 首先,即使Dodson小姐没有引用任何具体需要承担责任的法条,但她起诉Brown先生这个事情,你发现任何道德问题吗?大部分律师可能都没看到一个问题。即使之前并没有房东对其租户的狗的伤人行为负责,但在本案中,法院仍然可能判决Brown承担义务。毕竟,曾今有一段时间,房东对出租房屋的任何危险条件并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年才逐渐改变。新的规则和行为标准才在一个又一个案子中出现,但凡是总有第一次。正如Jerome Frank法官(一名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所述,法院在逐渐发展新的规则: 一个法院决定一个诉讼。这个法院有时候为判决附上一些理由。随着事实的发现,确定的法律后果随之而来。这些事实的结果依据普遍性的规则。然后,其他诉讼发生了。发现的事实与这个之前的诉讼很像、但又不完全相似。然而,法院运用了相同的概括和规则。在第三个诉讼中,事实看上去完全不一样,需要不同的概括或者对之前规则的例外。因此,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件判决,法院演变出法律规则。 对于Dodson小姐来说,普通法的问题在于:为了使法院判决房东有处理(如果他们可以)那些租客带危险动物进入租赁区域的义务,她如何找到一个可说服的法律依据? 当法院被要求决定一个“新的”问题时,法官应在心中牢记一件事,即哪种做法、习惯行为和期待是最能促进社会生活的。这些考虑十分依赖于Jones小姐、Brown先生、小Sarah生活的社区。有可能我们讨论的是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大城市的州;或者有可能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巨大的乡村州,这里的狗无秩序地生活在该州大部分区域,比如,强大的看护犬有效的保护了人民独立的生活和财产。当然保持粗暴的、多齿犬放在不同的区域,就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普通法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不需要我们预先地为所有我们之后可能遇到的真实情况来期待或者制作具体法律 取而代之的是,它可以轻松地塑造一个又一个案例来对应不同的情形和需要。随着知识、价值和公共道德的与时俱进,它也能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普通法无需等待立法机构察觉到法律漏洞、时代错误或者过时的规定,就能提供反映这些变化的法律判决。 虽然Sarah的案件可能是其中一个“第一次出现”的案件,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则,但法院仍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出判决。它不能让Sarah回去待五六年并看看是否有新的法律出台。法院必须用它现有的东西做到最好。当然,法院可以说:“因为Sarah Gardner的代理人没有引用房东就类似事实负责的案例,我们决定她没有权利要求赔偿”。它可以这样说,但这样的回应很可能非常令人不满意,为什么呢? 一个法官不应该简单地以不存在先例为由来拒绝一个起诉,其原因在于一个案件实际上从未有过完全一样的先例。没有两个案子是“完全重合的”(用律师的话来说);它们经常存在不同。因此,对法院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案例,而在于是否是一个足够类似的案例,一个案例的内在原则足以大到覆盖这个正在处理的案件。 比如,假设Dodson律师找到一些案例,法院判决房东对租客的客人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被租赁场所里各种危险的装置伤害了。然后,根据存在的“装置”案件,法官驳回Sarah的诉讼,仅仅是因为被狗伤害而不是装置,她就可以认为这几乎是不通情理的。虽然伤害的具体原因有区别,但原则是一致的。换句话说,Dodson女士能适用之前的“装置”案例作为类似的权威,来使Sarah具有普通法的权利而胜诉——即使没有直接相关的先例。正如现代法学理论者Ronald Dworkin描述那样: 即使不存在案件处理的既定规则,一方当事人也可能胜诉。在困难的案件里,发现一方当事人权利是什么,这依然是法官的职责,而不是追溯性地创造新的权利。 当没有适当的先例时,法官如何“发现”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是什么?正如Dworkin指出的那样,在司法实践中,即使不是直接适合的情形,司法判例也经常对后面的案子产生影响。一个先例可以是: 尽管早期判决的没有包含貌似能被解释成创造权利的语言,但它仍然被认为是有利于恢复权利。律师或法官会驱使这些早期的判决对之后的判决存在吸引力,尽管这些之后的判决并不在其特定轨道上。 换句话说,在之前的“装置”案例里,法律规则之内的法律原则也是法律的一部分,甚至这些先例并没有提及到被狗攻击的后果——即使在先例中的法官在做出判决时,并没有考虑到狗攻击时的情况。 Dodson小姐不一定被限制于她所在州管辖权以内的判例。在损害赔偿法(侵权法)的领域,法院特别希望从美国其他州的法律发展上找到指引,然后作为一个新的事实组合出现在它们自己的州里。每一个州有自己独特的普通法,然而,不同州的普通法倾向以相同或类似的法律原则作为依据。因此,来自各个管辖权区域的普通法司法判决将会是对其他普通法法院很好的“权利”判决的证据。 举个例子,假设Dodson小姐发现加利福利亚有一个案例:如果房东能够做出行为来摆脱这只攻击性的狗但他没有这样做时,房东对租客的狗伤人承担责任的。如果在Sarah所在州的侵权法基本上与加利福利亚的侵权法相似的话,Dodson小姐就有理由预测她的州法院很有可能会采用加利福利亚关于狗伤人的规则。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州法院经常自由地拒绝其他州的法律规则。然而,外州的判决(法律原则的证据、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部分普通法)具有法律权威性。法院通常把外州法院的判决至少看做是“可说服的权威”,即便它们没有“强制性的权威”(那就是,这些法院合法地被强迫遵循——通常被称为“有约束力的先例”)。 然而,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也只是法律的一部分。无论相关的法院怎么寻找间接的案例(比如“危险装置”),或者来自于外州的案例,法院仍然可能被说服不适用任何这些案例。相反,法院可能找到其他的法律原则,一些压倒一切的原则。比如,房东Brown的律师可能向法院强调,有一些对Sarah不利的隐私问题。他可能争辩说,对Sarah的判决可能会引起房东干涉租客的生活习惯的选择,比如尽量让租客不要带宠物。Brown的律师可以说服法院,如果法院支持Sarah的话,大量的房东就会给租户说:“要么狗走,要么你走”。换句话说,他可能说服法院,让法院区对“装置”案例进行区分,认定租客错误行为的狗与危险物品之间应当具有法律上的区别。 律师和法官通过强调某些事实(在先例和现实案件中的事实)来“区分”先例,这些事实导致了先例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因为对那些可能被考虑到现实生活的法律问题的相关因素没有理论的限制(类比是律师必须学会“感知”的东西),涉及非常广泛的先例在任何既定案件里,能够作为可适用法律的一部分被引入。在决定是否将“装置”案件扩大至狗咬时,法院可能会参考一些案例,这些案例涉及掉落的石膏、看门狗、挠人的猫、踢人的马以及隐私权等等,也许,这些案例并非一定涉及房东或者甚至人身伤害。可以想象,上述任何案例可能建构出房东行为的标准和准则,伴随着租客的狗咬人,这些行为应该是 “被法律承认”的。因此,Dodson律师和Brown的律师必须找到这些潜在的、可适用的案例并决定如何使用它们。 除了区分案例外,法院也有其他的事要做,使它们能够处理先例,并根据它们所理解的、更合适的公共政策来塑造法律。比如,Brown的律师发现一个1842年的案例,法院称房东不需要对租客的马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该马逃脱并吃掉邻居的茶花。如果一个先例来自于5年或10年以前,它可能被认为比来自100年以上的先例更加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根据案件的领域——在一个缓慢发展的领域的话,比如所有权法,一个十九世纪的案例可能特别的“接近当代”,然而来自相同年代的劳动法或者民权案例可能并没有判例价值。这个165年的“茶花”案例仍然是法律的证据,但它的权威性很可能受到怀疑,尤其是如果反对方能指出在此期间的条件已经发生显著的改变。
*** 现实的法官如何看待美国普通法、立法、以及使判例具备“法律”般的“约束力”的发展呢?在当代,就先例被实际对待的方式来说,在“制造法律”和“发现法律”之间的整个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小题大做。我们会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个相关的当代意见做扩展引用,来结束本章。这里Alex Kozinski法官采用了遵循先例原则的迷你论文的形式,来作为他从普通法中提炼后,留给我们的并成为我们当代的遗产。
Hart v. Massanari 266 F.3d 1155(9th Cir. 2001) 巡回法官KOZINSKI 普通法法官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制造法律,相反,他们通过具备相似事实的先例的帮助来“发现”法律。法律是什么?有一个观点可以作为证据,但它并非独立的法律来源。参见Theodore F.T. Plucknett,《普通法简史》343-44(5th ed.1956)。法律看上去作为一种独立于法官所说的存在:“没有人创造的一个奇迹,只是偶尔由法官宣布”。2 John Austin,《法学及实证法学哲学的讲座》655(4th ed. 1873)(重点略)。意见仅仅是法官试图确认法律的努力,与科学实验来确定自然规则的努力很类似。如果一个十八世纪的法官相信先例是错误的,他就会说这个先前的法官在试图辨别法律时出错了。参见Bole v. Horton,124 Eng. Rep. 1113, 1124(C.P. 1673)。法官和律师都不认为先例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约束力。
* * * 在十九世纪中晚期,一个英国法官可能忽略上议院的决议,直到1842年末,财政部和女王法院对同一个问题仍持有不同的看法。普通法法官把先例只是作为政策或实践的例子,一个单独的案例通常不存在约束力。
* * * 比起制造法律,法官宣布法律的观点在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仍然根深蒂固。Blackstone,他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20年就撰写了评论,他也被制宪者们极大的尊重和跟随。他提出“法律”和“法官的意见”并非同一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法官会犯法律错误,在这些案例里,先例并非单纯的法律。1 William Blackstone,评论 70-71(1765)
* * * 有约束力的判例的现代概念——针对一个法律具体的点,单个的意见创立了一个进程,同级或者位于法律金字塔体系的下级就应该遵循它——只是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才开始出现。律师开始相信法官创造法律,而不是发现法律。同时,搜集案例和其权威报告程度不断提升。随着法律的概念发生变化,更综合的报告体系开始出现,使司法判决具有权威约束力成为可能。
* * * 然后,Kozinski法官对美国联邦法院里的判例法中的一些细节做了描述。 当出现新的法律问题时,联邦法院一般会考虑其他法院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这个考虑将不限于同等级、更高级法院、甚至相同法律体系的主权国家的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会引用地方法院的判决,尽管它们属于其他巡回法院辖区内;最高法院可以引用下级法院的判决(省略引用)。它也经常引用外国法院的判决,只要它们在本国法院之前涉及了相似的事情(省略引用)。这个过程甚至扩大到了非判例的权威,比如论文和法律评论文章(省略引用)。 当然,引用案例并非完全遵循它;在“博学的同事”的五个字内“尊重地拒绝”几乎是陈词滥调。在仔细考虑和消化其他法院和评论者的意见后——经常在新型法律问题上给出一些互相冲突的指导——然后,法院将沿着一个或另一个权威路线,或者有时候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然而我们认为忽略相反的权威甚至不承认其存在是种不好的形式,很容易理解——有约束力的判例不存在时——比起之前考虑过该问题的先例,法院可能开拓一条不同的道路。只要先例的权威被承认并被考虑,法院就被认为遵循了普通法的义务。 但是,在今天的联邦法院,先例也发挥着一个非常不同的作用,与法院的横向和纵向组织有关。参见John Harrison,《国会对判例规则的权力》,50 Duke L.J. 503(2000),一名地区法官不可以尊重地(或不尊重地)拒绝他那博学的同事,该同事在法官自己的上诉法院里裁定着法律问题,或者跟随最高法院大法官对主要的法院做着记录。在该体质内,不能考虑抛弃约束力权威;它不仅是“法律是什么”的证据,更是“判例法就是法律”。如果一个法院必须按照先前的、具有约束力权威的意见来决定一个问题,之后的法院必须得出相同的结果,即使它考虑了一个不明智或者不正确的规则。约束力权威必须被遵守,除非或直到被有能力的机构推翻。 在决定是否必须遵循先前的判决时,法院不仅仅考虑“案例的理由和精神”,也要考虑“具体判例的文字”。Fisher v. Prince,97Eng. Rep. 876,876(K.B. 1762)。它不仅包括了宣布的规则,也包括了引起争议的事实,其他被考虑和被拒绝的规则,以及对任何异议或者同意所表示的意见。因此,当制定约束力权威时,所使用的精确语言通常对所宣布的规则的轮廓和范围是很重要的。
* * * 显然,约束力权威是非常强大的灵药。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控制法律的各个角落,除非或直到最高法院自己推翻或修改它。下级法院的法官可能发出它们的批评声,但必须还得遵循。参照,e.g.,Ortega v. United States,861 F. 2d 600,603&n. 4(9th Cir. 1988)(这个案件完全被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所控制…我们同意这个上诉人应得到政府更好待遇的不同意见。不幸的是,司法先例剥夺了我们为行使公平而享有得自由裁量权)。巡回法院权威也是如此,虽然它通常覆盖的地理区域要小得多。巡回法律…约束了内部的所有法院,包括巡回法院本身。因此,率先考虑一个法律问题的审判会议,其不仅仅为巡回法院内部的全体下级法院创造了法律,也是为了该法院未来可能出现的审判会议创造了法律。
TBC. 《Whose Monet?》于每周五更新。
刘汛律师,重庆鼎圣佳程律师事务所金融法律服务部律师,于2019年至今,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